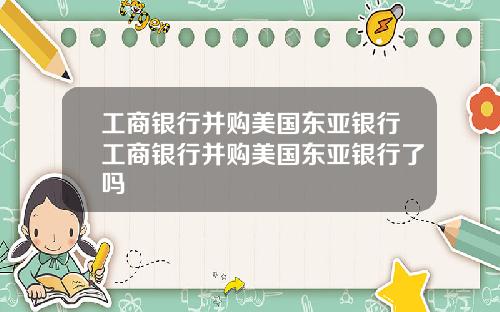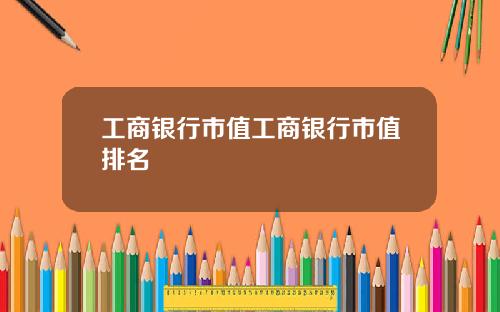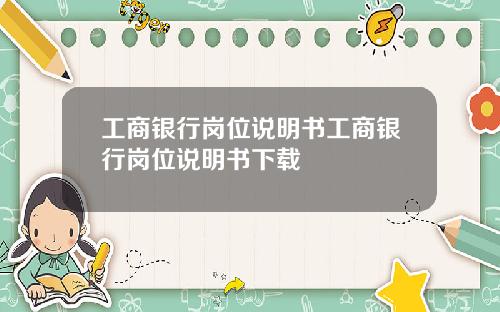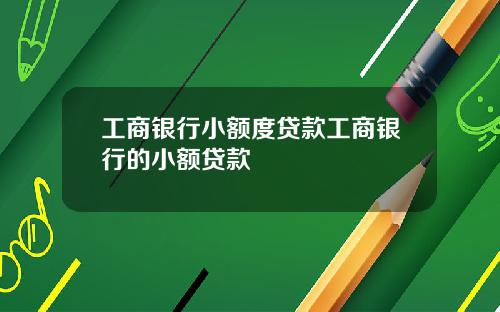【推荐】中国海洋水产养殖净碳汇时空演变及其影响因素-海洋养殖业股票资讯网站
海洋养殖业不仅具有可观的经济效益,而且为碳中和提供了优质的“脱碳空间”,对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两阶段LMDI(对数平均分割指数)方法,从养殖结构、养殖效率、养殖规模、贝藻竞争力和养殖模式五个因素综合分析了我国海水养殖净碳汇容量的形成机制。
结果表明:1)2010-2019年,中国海水养殖净碳汇逐年增加,三个海洋经济区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空间分布特征。2) 养殖效率的提高和养殖模式的创新对碳汇的增加贡献最大,技术进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 贝类和藻类的竞争力较弱,严重阻碍了碳汇的增长速度,是碳汇空间日益紧缩的主要原因。4) 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海洋水产养殖碳汇增加的机制具有区域异质性和资源依赖性。基于这些发现,提出了强调海洋水产养殖生态价值、加快深海海洋水产养殖技术创新、提高组织体系和管理水平、扩大海洋碳汇空间的策略。
1简介
根据联合国《蓝碳报告》,海洋生物的蓝碳占地球生物碳的一半以上(55%)。尽管水产养殖中碳汇的概念尚不清楚,但Krause Jensen和Duarte(2016)指出,藻类可能是海洋沉积物和深海固碳的重要来源。藻类可以通过光合作用或吸收溶解的营养物质,将海水中溶解的无机碳转化为有机碳,从而促进大气中CO2向海水中的扩散。贝类可以利用海水中的碳酸氢盐形成碳酸盐外壳,其固碳过程起到生物泵的作用,也加速了大气中二氧化碳向海水的扩散。因此,贝类和藻类的养殖对碳循环有明显的影响,可以通过捕捞成为“可移动的碳汇”,这对提高海洋的负排放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大陆海岸线1.8万公里,海域面积470万平方公里。中国对水产养殖碳汇的研究已有十多年的历史(Zhang等人,2021)。许多研究人员从环境、经济、养殖方式、养殖物种等多个角度分析和论证了水产养殖中的碳汇(Tang et al.,2011;Tang and Liu,2016;Jiao,2021),海洋养殖正以其可观的经济效益和蓝碳独特的生态价值日益成为“碳汇领域”。然而,海洋养殖业长期以来一直因环境污染而饱受批评,是近海水域的重要“污染源”。海水养殖生产的劣质设备造成的养殖污染、抗生素、生长激素污染、水体交叉污染和泡沫污染,导致了沿海富营养化和水环境恶化的严重问题。2019年,包括中国农业农村部在内的十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水产养殖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鼓励发展非饲料滤食性贝类和藻类,并为“增加碳汇”和“控制污染”指明了方向。
我们的研究做出了一些贡献。首先,基于海洋水产养殖发展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约束,系统地识别了中国海洋水产养殖碳汇的时空特征和演变。其次,本文重点研究了贝类、藻类等具有高效固碳和无诱饵的“碳汇渔业”,系统分析了海洋养殖净碳汇的影响因素和机制及其对下沉贡献的演变。再次,本文对拓展海洋水产养殖净碳汇空间,促进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2节回顾了相关文献,第3节描述了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第4节分析了实证结果,第5节给出了本文的结论和建议。
iao等人(2010)、Jiao和Xu(2018)指出,微型生物碳泵可能是一种重要的未开发碳汇,对实现海洋碳汇功能具有很大的应用前景。许多学者计算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藻类的固碳能力。例如,日本藻类的平均固碳能力为每年1.3吨/公顷(Muraoka,2004),澳大利亚沿海藻类的平均固碳能力为0.4吨/公顷每年(Filber Dexter和Wernberg,2020),中国东部海藻的固碳能力是渤海、黄海和南海的2.4倍、1.2倍和8.2倍,分别(Shao et al.,2019b),通过室内培养发现麒麟的碳固存率为每年每公顷16–68吨(Erlania和Radiarta,2015)。贝类养殖被认为具有更高的碳汇效率和更长的碳汇循环,被称为最有前途的“海洋过滤器”。特别是,通过手工加工、填埋或沉淀到沉积物中,贝类的外壳可以被长期封存,成为更稳定的碳汇,并在贝类生长过程中被摄入和分解后被掩埋。
海洋碳汇被认为是最具潜力的碳汇活动(Tang和Liu,2016),是海洋养殖业升级和渔业产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Xu et al.,2018),也是实现海洋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Yu et al.,2018.)。中国率先提出渔业碳汇概念,积极倡导低碳渔业。根据Tang(2011)的研究数据,1999年至2008年间,中国每年通过贝类养殖从水体中去除440万吨二氧化碳,相当于每年平均50多万公顷的强制造林,节省了近400亿元的国家造林投资。学者们对海洋水产养殖碳汇容量的估算方法以及碳汇渔业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
渔业物种碳汇容量的计算更为复杂(Pershing et al.,2010)。初始估算方法主要利用能量预算模型,利用海洋水产养殖中贝类和藻类的摄食能、粪便能、排泄能、代谢能和生长能,估算贝类和藻类碳汇产量(Zhang et al.,2005)。随着对渔业碳汇机制的进一步了解,学者们开始利用不同藻类生长过程中释放的溶解有机碳和颗粒有机碳比例与光合作用中固碳的经验系数来计算藻类的碳捕获量(Yan et al.,2011),或者通过渔业食物链中各级的生态转化效率来计算最终捕获量(Zhang et al.,2013),从而推断贝类和藻类的固碳能力。近年来,学者们逐渐统一了碳汇容量的计算方法,即利用贝类和藻类的产量和含碳量来计算它们各自的碳汇容量,并将其相加以获得碳汇容量(Qi et al.,2012;Shao et al.,2019a;Zhang et al.,2020)。
目前,海洋水产养殖碳汇容量的测量主要分为两个维度。一种是从材料质量的角度,或侧重于藻类碳汇容量的估计(Alvera-Azcárate et al.,2003;Mitra et al.,2014;Quan et al.,2014.),或将估计范围扩大到贝类和藻类碳汇能力的估计(Shao et al.,2019b;Xu et al.,2020);其次,从渔业碳汇价值的角度,估算贝类和藻类碳汇的经济价值(Yue et al.,2014;沈和梁,2018;Yu et al.,2020),以探索碳汇渔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Smith(1981)指出,大型藻类的碳汇产量可能在实现全球碳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从那时起,学者们广泛探讨了藻类碳汇容量的影响因素,并认为水产养殖的成本(Alpert et al.,1992)、人工养殖的方式、营养是否充足,甚至碳是否由于藻类收获的人工干预而移出水中(Orr和Sarmiento,1992)都是影响藻类碳汇能力的因素。我国研究人员研究了影响海洋水产养殖碳汇能力的诸多因素,如水产养殖模式、渔业产出技术水平(孙和赵,2011)、资源投入、经济增长、环境影响(张等,2020)、水产养殖产量、水产养殖结构(季和王,2015)、水产养殖业物种(杨等,2021)等。这些研究侧重于发展海洋水产养殖技术,并讨论了其对海洋水产养殖碳汇输出的影响。
目前,对碳汇市场的研究仍集中在草地和森林等陆地生物碳汇领域,相关研究探讨了供需的影响因素和碳汇市场运行机制(Pfaff et al.,2000;刘和高,2012;卢和张,2014),而基于市场的海洋水产养殖碳汇机制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Xu等人(2017)调查了山东沿海地区的养殖业主,发现养殖户参与海洋养殖碳汇的积极性不高,主要是因为碳汇渔业的生态补偿制度不完善。Xiang等人(2017)调查了山东省威海市海洋水产养殖碳汇发展现状,发现海洋水产养殖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导致水域自净能力超过,严重制约了碳汇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海洋养殖产量高、规模大、品种多、营养水平低、生态效率高(Zhang等人,2021),海洋养殖碳汇是“碳篮子”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由于海洋生物资源之间碳转化效率的差异,海洋水产养殖生产力与净碳汇容量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目前,碳汇渔业的理论研究滞后于海洋养殖业的实际发展。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海洋水产养殖的经济价值,很少考虑资源和生态约束下碳汇渔业的生态价值。特别是,缺乏基于养殖规模、养殖结构、养殖模式、养殖效率、贝类和藻类竞争力等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系统研究,也缺乏基于此的净碳汇机制和净碳汇系统解决方案的综合分析。本文采用两阶段LMDI(Logarithmic Mean Divisia Index)方法,从养殖结构、养殖效率、养殖规模、贝类藻类竞争力和养殖模式五个主要因素,综合分析了中国海洋养殖碳汇容量的时空特征、演化规律和影响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碳汇政策,对拓展海洋碳汇空间具有重要意义。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net carbon sink in marine aquaculture in China
- 版权所属:理财广场
- 本文地址:http://www.cj8818.cn/105875.html
- 版权声明:版权声明:本文内容由互联网用户自发贡献,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本站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不拥有所有权,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如发现本站有涉嫌抄袭侵权/违法违规的内容, 请发送邮件至 931614094@qq.com 举报,一经查实,本站将立刻删除。